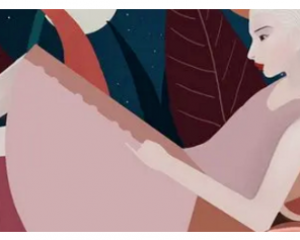2022年8月,清醒的觉悟到,我的爱情死于你的唇齿之间,葬于我的九幽心田。一年前的这天,庆幸仿佛置身于爱的转角,而如今犹如昨日重现,只是挥别的一种延续,整整一年如偷来一般,爱恨酸甜,终究要还。
1984年,我生于河南西部山村,一个穷困的家庭。对幼儿时期的记忆,仅是大人说的一场死里逃生。不知为何被卡住喉咙,送到医院时眼睛发直,针扎破手指流出浓黑的血,命悬一线,后来不知道怎么救过来的,也许是上天眷顾命不该绝,又或者是命硬阎王不收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不知道所谓的后福,是不是三十多年后,万念俱灰的时候遇见你,这是后话,只能娓娓道来。
1990年,六岁的我被送去上学前班,家里一张死沉的大方桌和一个小凳子,成了我一年的伙伴,大方桌与其他孩子的桌子格格不入,就这样伴我度过了一个春秋,爱捣乱成了我学前班的代名词,不讨老师喜欢。
1991年,当第一批九零后断奶时候,我光荣的进入小学,前三年不知学习为何物,闭塞的乡村,破落的学校,贪玩与调皮是每个孩子的天性,稀里糊涂的读完了一二三年纪,记忆最深的是学校要建图书馆,要求每个学生捐三本故事书,家里穷的没有一本书,交不上来又不愿跟家里人说,几次推脱后就被赶出课堂,直到后来妈妈拿着三本新买的故事书交给老师,我才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放学我趴在水泥扶手上,用指甲使劲的划,疼得眼中噙着泪,那三本我都没看过的故事书,花了家里十几块钱,将近一学期的学杂费,至今我都记得其中一本的名字,海的女儿,因为是我隔着塑料袋看到的,所以记忆犹新。
转眼进入四年级,学习成绩不知怎么回事,数学年纪数一数二,语文一般,也许是得益于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,总成绩也能进入前五,经常测验发本子,以至于从今以后再也没买过练习册,甚至大学了还能分崭新的本子给邻居小孩用。这一年1994,我第一次登上领奖台,年级第四发了一个小笔记本,至今仍躺在我远在老家的百宝箱里。这一年真不平凡,是脑袋开了窍,还是冥冥中注定有些事发生于远在天边。就这样过完了小学,自然而又平淡。
记忆里的童年是妈妈夏天担着一担西红柿,卖完换得十几元钱,冬天乘着别人家的三轮车,到远处走村串街,十几斤的一颗大白菜卖了几毛钱。没有电视机,只能到别人家蹭看,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春晚能到别人家看我都不看,因为觉得家里人看不到,有种不愿独享的凄惨,或许正是因为如此,往后这么多年一直庆幸没有近视。
初中增加了很多科目,比起小学的语文数学,很多人适应的手忙脚乱,不写作业经常挨批,一直保持着成绩中上熬到了初三。恰逢村里更换农业电,220元的费用成就我半年多的黑暗时代,虽然我从没在家写过作业,却经常望着院子上方的白月亮感慨,穷最伤人心。因为我初一曾因交不起几十元的学费而离家出走,觉得学习无用,直到初三英语老师的点醒,不学习你能干啥,还有几个被劝退不参加中考的同学,我忽然想不能消沉于命运的安排,底子加努力考上了市里的高中,开启了下一段颓废的学习旅程。
记忆里的千禧年,开启了高中寄宿时代,终于脱离了家庭,一周回去半天,三年来我从不住家里,似乎有种长大的感觉,虽然一周只有二十几块生活费,但我每个月都会有结余,我想已以备不时之需,因为穷怕了。